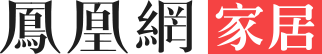《北辙南辕》被嘲太假?老北京胡同的生活是真的!


独家抢先看
冯小刚导演的电视剧《北辙南辕》,一开播就是话题中心。
《北辙南辕》海报
几集看下来,都顾不上剧情,光忙着数里面的明星大腕了。
这部电视剧的热,有一大部分来自于争议,大家纷纷吐槽说,太不接地气了!冯导是有多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。
比如王珞丹饰演的女老板尤珊珊,看起来挺闲的,一天到晚跟人吃饭聊天就把钱挣了,人家欠她几千万她发个善心就不用还了,她和几个女友没有深交就拉着她们开餐馆,启动资金都可以借;还有司梦这个角色,看似要反映家庭主妇的困境,可要能住上像她家那样的北京黄金地段的大房子,还哪儿来的困境啊……
尽管电视剧槽点多多,但我一下子就被镜头中的老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种草了。
蓝盈莹饰演的小演员鲍雪,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她穿过胡同,推门进入四合院里的家,院子里孩子们在嬉闹,奶奶在侍弄花草,爷爷在闲坐乘凉,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
(《北辙南辕》截图)
司梦追着尤珊珊还钱包的这场戏也是在胡同,她们车子停下的地方,就是国子监附近的成贤街。
(《北辙南辕》截图)
尤珊珊转进她的“灵魂伴侣”黑哥的家,原来在胡同里,还能藏下如此气派的工作室。
(《北辙南辕》截图)
二人找了个小咖啡馆聊天,如此文艺范儿的小店,在露台上能看到老房子的屋顶,这只有在北京胡同里才能享受得到。
(《北辙南辕》截图)
胡同,是北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,一条条胡同,见证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变迁,贯穿着北京名流和市井生活的脉络。
老北京人说:“有名的胡同三千六,没名的胡同赛牛毛。”根据1946年的统计,北京共有胡同3065条。
胡同这种北京特有的传统建筑形式,最早能追溯到元朝。元代建都时是先规划后建设的,沿河而建非常整齐,宽二十四步为大街,宽十二步为小街,宽六步则为胡同。“胡同”这个词也是蒙古语的音译,意为“水井”,有人住的地方自然要有水井,于是它渐渐成为人们居所的代称。
电影《邪不压正》剧照
胡同里的四合院,是一个理想的居住样本。
作家冯唐在后海有个四合院,这里几乎完全符合他在《我的理想房子是挤满朋友的小房子》这篇文章中对理想居所要素的描述:所在城市要有历史,房间面积要小,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,要有景色,附近要有公园、大学、朋友,要有足够好的生活设施。
冯唐的四合院
但现实中普通百姓的胡同生活,恐怕没那么浪漫,更贴近于20年前的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中的描述,一间房要挤下几口人,“进屋就上炕”,家里往往没有独立卫生间,光如厕和洗澡两件大事,就困扰了老城居民数十年。
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剧照
为了既能保住老北京的味道,又能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,北京一直在实施“城市更新”——在不大拆大建的框架下,通过市政改造、功能补齐和现代设计的引入,让胡同生活面貌发生改变。
现代与传统相碰撞,一场漫长的实验正在展开。
更有很多操盘国际级大项目的知名建筑师,在北京胡同里留下一个个小而美的作品。
青山周平:
用10年读懂胡同生活
青山周平,是近年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新生代日本建筑师,他对于胡同的了解甚至超过很多地道的老北京人。2005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,他选择做一个“北漂”,在北京胡同里安了家。
青山周平觉得,胡同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,邻居家的小孩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家,这在公寓楼里简直不敢想象。
胡同生活给了青山周平很多设计上的启发:胡同里的家面积不大,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室外进行的,房子可以特别小,但是生活却更加丰富,这才是理想的家的状态。
厨房很小,但出门就能买到最新鲜的食材;附近有很多好吃的餐馆,家里有没有客厅也无所谓了;家里就算没有办公的地方也没关系,可以去离家不远的咖啡馆……
青山周平在北京的家
青山周平在北京的家
以胡同的生活为灵感,青山周平设计了“400个盒子”共享社区,私人空间只是一个大约5平方米的小盒子,外面的整个空间都是共享的,让住在里面的人很有归属感。
“400个盒子”展区
青山周平也做了不少胡同改造的项目。这个名为“树下屋”的院子,被改造成了一家民宿,原来的8户人家住的空间被改造成6间客房。
一进院就看到一面墙壁,上面的老青砖是保留下来的,背后隐藏着楼梯,拾阶而上就能到达屋顶天台。院落的设计既是现代的,也延续了一些传统,院子里的生活空间相对开放,邻里之间可以交流,而民宿房间则是私密的。
为家具店“失物招领”做店铺设计时,青山周平把原本的商业空间变成了一个胡同里的家,这里成了无数北京文艺青年的周末杀时间胜地。
马岩松:
把先锋建筑嵌入北京胡同
马岩松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人,从小在四合院里长大,是胡同里的“孩子王”,长大后,他把自己的先锋建筑理念带到了老胡同里。
比如去年频频被媒体报道的,建在四合院里的幼儿园。新建筑连接了原址的老四合院、老树还有天空,孩子们可以在彩色的跑道上“上房揭瓦”,启发他们思考和追逐不同的可能性。
马岩松说:“老北京有很多‘缝隙’——地道、屋顶、院落等。在这里,自然成了主体,建筑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”
“胡同泡泡218号”是马岩松最新的一个北京旧城改造项目,秉持“不动、更密、针灸、精神”四个原则。项目对位于北京前门东区的一座清末四合院进行了修复、改造——在恢复四合院原有三进格局的同时,创造性地加入了三个不同形态、犹如天外来物的“泡泡”。“泡泡”由不锈钢打磨制作而成,里面是会客室和共享工作空间。
泡泡光滑的表面折射着院子里古老的建筑、树木以及天空,与旧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马岩松说:“这是一种“微观乌托邦”式的理想,我希望这些“泡泡”像新生的细胞一样具有生命力,赋予老建筑活力,并通过改变局部而达到复苏整体社区的效果。”
张轲:
为北京胡同的存留而努力
曾获得阿尔瓦·阿尔托奖的张轲,是中国新一代建筑师的代表。
1990年代在清华读书期间,张轲就对北京老城遭受的“温水煮青蛙”式的破坏表示很担忧。他在论文中提到,现代化对于古城的破坏不像战争时期那样强烈,但就在你觉得越来越舒适的同时,一些建筑文化就被毁掉了。
成为建筑师之后,张轲以胡同中的院落为切入点,致力于将微小空间变得宜居。
白塔寺旁的一个150平方米的大杂院,经过张轲的改造后,变成了一个“共生院落”,此项目目的是探索公共空间与私人融合的可能性,打造胡同里的小尺度舒适空间。
“微胡同”项目,改造了杨梅竹斜街的两个大杂院,把其中一个40平方米的老房子改造成了一个被五个房间交错围绕的庭院,还加入了极小的卫生间、淋浴和厨房等模块。
2012年张轲受西城区政府邀请,将大栅栏一个污水横流的大杂院改造成了让他声名大噪的“微杂院”。院落中保留了原有的一棵大树,还加进了一个公共图书馆,成了一个“微尺度”的社区空间。
隈研吾:
北京工作室就在胡同里
日本的建筑师隈研吾干脆把北京的建筑设计工作室放到了胡同里。
从西打磨厂大街一进来就能看到隈研吾招牌式的设计元素,建筑外立面用灰色的金属模仿了北京传统建筑的花窗元素,若隐若现的玻璃幕墙和传统的灰色的砖墙对半分开。
原有的木结构被保留并修复,与铝制构件和玻璃幕墙形成对比,将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了一起,完美地把建筑工作室“嵌”到了胡同的老房子之间。
隈研吾说,老北京充满了历史悠久的胡同和四合院,如今大多数已被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取代,他的团队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种低层传统建筑的新型存在方式。
城市更新,
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
建筑师们大胆地把现代设计理念引入传统的胡同院落,探索在传统胡同有限的空间中,打造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。
很多胡同里的先锋建筑成了网红打卡地,但也有一些胡同里的老居民表示,这些建筑“很漂亮,但不知道有什么用”。
正在胡同里进行的城市更新计划,可以说是一场建造实验。一些设计如果没有很好的用途,可能以后也会被拆除,然后再引入其他设计。设计师们一直都在探索最好的方法。
建筑师庄子玉的工作室也在北京胡同里,他们工作室的屋顶,承载了许多生活要素,这是对北京这座古都更浪漫的表达。
北京也曾经历大拆大建的过程,20世纪90年代中期,每年有将近600条胡同消失,比如前门大街就彻底变成了商业街。
好在,2017年出台的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16年——2035年》)明确指出,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和四合院,推进历史文化街区、风貌协调区及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的保护和有机更新。
“有机更新”替代了“老城改造”,成为老城发展的方向。如今,我们正在很细致地像绣花一样做城市更新。
在胡同中注入新的活力,不是完全以“新”取代“旧”,也不是一味保留传统而拒绝去拥抱新的生活方式,而是一种城市生命力的延续。新旧共存、拥有不同的生态才是胡同应有的面貌。
这场城市更新的实验,或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。建好一座北京城,我们还在路上。
(文章来源 凤凰空间,侵权联系删除)
“特别声明:以上作品内容(包括在内的视频、图片或音频)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“大风号”用户上传并发布,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
Notice: The content above (including the videos,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)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,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.”